城市在人类文明演进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学术界在探讨古代文明起源时,即把城市的出现作为文明起源的标志之一。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对先秦时期的城市生活多有记录,展现了当时城市文明的许多画面。西周开国之初,是我国第一次城市建设的高潮。凉州城大规模的营建当在前凉,通过这次营建,成为西部的大邑重镇。城市的繁荣又反过来促进诗歌的发展,城市生活的印记不可避免地表现在诗歌中。西部古城凉州,是丝绸之路上一颗璀璨明珠,历史文化源远流长,曾是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驿站和商埠,是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融汇、传播和辐射之地,由此而形成的凉州文学艺术,以其独特的风格丰富了文学艺术宝库。咏凉诗是凉州文学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多篇描写城市生活,折射出当时城市生活的风貌。今天,我们欣赏咏凉诗,既可以从中享受古凉州都市生活的丰富多彩和浪漫情调,领略其博大雄奇、悠久厚重的文化底蕴,但又为其的衰落而悲悯哀叹。然而,这就是历史,这就是世界上许多城市盛衰荣枯的缩影。
温子升笔下的凉州:西部大邑,繁华都市
温子升(495-547),字鹏举,济阴冤句(今山东菏泽市)人,祖籍太原,东晋显贵温峤后代,北朝著名文学家。北魏孝明帝初,在全国选拔辞人补充御史之职时,他在800名应考人中名列榜首,一举成名,补为御史。他在北朝极负才名,与当时的文学家邢劭、魏收齐名,时称“北地三才”。明人辑有《温侍读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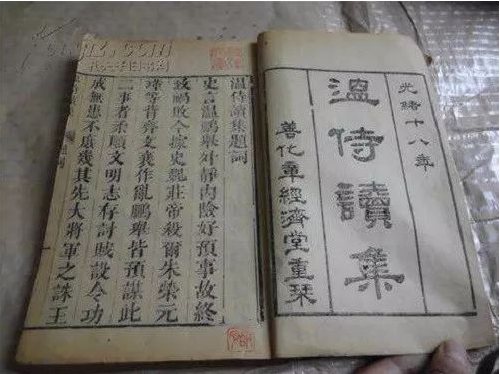
《温侍读集》
温子升的诗作明显地从南朝诗歌中学习借鉴了不少有益的成分,也受到西凉音乐的影响。《凉州乐歌(其一)》描写6世纪的凉州都市生活,极富特色:远游武威郡,遥望姑臧城。车马相交错,歌吹日纵横。
这是一首在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把“武威”地名写入诗歌的名作。武威,又名姑臧,亦称凉州。十六国时的前凉、后凉、南凉、北凉及唐初的大凉政权曾在此建都,是古代中原与西域经济、文化交流的重镇。温子升生活于北朝,那时军阀混战,北方少数民族崛起,并登上政治舞台,各割据政权之间战争不断,人民饱受离乱之苦,百姓期盼太平。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温子升凭一腔追慕昔日繁华、撷取凉州安乐记忆的“郁然特起”的豪情,写下了《凉州乐歌》二首。
《凉州乐歌》是乐府体裁的诗篇。前两句属写实,写远景,大处落笔,从视觉写诗人走了很远很远的路,出关西,渡黄河,越过终年积雪的乌鞘岭,在一片绿色环抱的土地上,远远地看到了一座雄伟的城市,它就是武威郡的治所—姑臧城,即今天的武威城。后两句属夸张的写实,写近景,从触觉、听觉写远方的游客进入姑臧城,只见香车宝马,熙熙攘攘,往来不绝;在华丽的馆舍酒肆之中,羌管悠悠,歌声悦耳,此处歌歇,彼处舞起;全城到处是歌舞的海洋,商贾的天堂,凉州人沉浸在歌舞升平之中。
这首诗最显著的艺术特点就是有别于南北朝诗人沉郁悲凉的哀怨情绪,突显北歌豪放刚健之气。王夫之评论温子升《凉州乐歌》类诗作云:“江南声偶既盛,古诗已绝,晋宋风流仅存者,北方一鹏举耳”(《古诗评选》卷5)。北魏司空、济阴王元晖业曾说:“江左文人,宋有颜延之、谢灵运,梁有沈约、任昉,我子升足以陵颜轹谢,含任吐沈”(《魏书·温子升传》)。明人胡应麟评论说:元晖业的话“虽自相夸诩语,然子升文笔艳发,自当为彼中第一人”(《诗薮·外编》卷2)。其作品传至南朝,梁武帝萧衍大加赞赏,直谓:“曹植、陆机复生于北土。”北魏阳夏太守傅标出使吐谷浑,“见其国主床头有书数卷,乃子升文也。”足见温子升的诗文在当时影响之大。
我们从温子升的这首诗可以看出,1400多年前的凉州,已经是一个经济文化相当繁荣的城市,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凉州的都市生活已达到了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协调发展、同步发展,不仅是区域政治中心,也是经济中心、文化中心。
岑参笔下的凉州:民族融合之地,建功立业之都
岑参(715-770),原籍南阳(今属河南省),移居江陵(今属湖北省)。少年时读书于嵩山,后游京洛河朔,隐居终南别墅。天宝三年进士及第,后入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北庭节度使封常清等戎幕任职十余载,并在武威驻过一段时间,对边塞生活深有体验。由于边塞军旅生活较长,又长期往来于凉州、安西、北庭等地,其诗以边塞诗著称,写西北边塞风光、将士生活和西北战场的奇异景色,气势磅礴,昂扬奔放,语言变化自如。他是盛唐边塞诗派的代表诗人,与高适并称“高岑”。有《岑嘉州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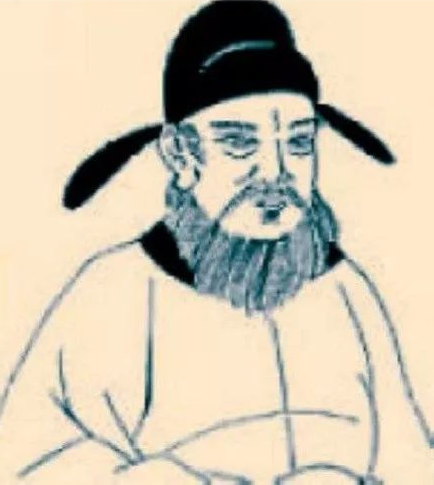
(岑参像)
天宝年间,唐王朝国力强盛,社会安定,边疆绥靖,各民族之间互相往来,关系融洽,岑参及同时期的诗人对安定边疆、建功立业充满信心,情绪豪迈、乐观,他们从一种欣赏的态度和喜悦的心情去领略边地风光、感受异域生活。其《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通过对西部重镇凉州的一次朋友聚会,描写了盛唐时期凉州繁华而又充满浓厚文化氛围的都市生活,抒写了自己的抱负,表现了一种昂扬向上、奋发进取、以天下为己任的自觉自励、自信自强的精神状态。诗曰:弯弯月出挂城头,城头月出照凉州。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琵琶一曲肠堪断,风萧萧兮夜漫漫。河西幕中多故人,故人别来三五春。花门楼前见秋草,岂能贫贱相看老。一生大笑能几回,斗酒相逢须醉倒。
天宝十年(751),高仙芝改任河西节度使。此时,岑参暂驻凉州,结识了不少朋友。两年后,哥舒翰任河西节度使,其僚属如高适、严武等也与岑参是老熟人,所以当天宝十三年(754)岑参赴北庭途经武威时,就有很多老朋友前来迎送。此诗写的就是与河西幕府的老同事、老朋友的一次欢聚夜饮。诗中写了凉州的边域风光、民族杂居的习俗民情,更把夜宴写得兴会淋漓,豪气纵横,洋溢着盛唐的时代气息,体现出当时读书人奋发有为的人生态度。
“弯弯月出挂城头,城头月出照凉州。”首先出现的是城头弯弯的明月,然后随着明月升高,银光铺泻,出现了月光照耀下的凉州城。首句“月出”,指月亮从地平线升起,次句“月出”,指月亮在城头上继续升高。“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这是随着月光的照耀,更清晰地呈现了凉州城的全貌。盛唐时的凉州是与洛阳、扬州、广州、汴州等城市并列的第一流大都市,是西北地区仅次于长安的通都大邑。“七里十万家”,正是大笔淋漓地勾画出这座西北重镇的气派和风光。凉州处在边塞,居民中少数民族和西域各国的胡人很多,他们能歌善舞,多半都会弹奏琵琶。不用说,在月光下,胡汉杂居的凉州城荡漾着一片琵琶声,表现出另一番景象:不仅人烟稠密,而且胡乐盛行;地域的辽阔,风俗语言的差异,战争的恩怨,都未能阻隔胡汉民族的融合和文化的交流。诗人在这里写出了凉州城的歌舞繁华、和平安定,同时带着浓郁的边地情调。“琵琶一曲肠堪断,风萧萧兮夜漫漫。”仍然是写琵琶声,但已慢慢向夜宴过渡了。这“一曲琵琶”已不是“胡人半解弹琵琶”的满城琵琶声,乃是指宴会上的助兴演奏。“肠堪断”形容琵琶声动人。“风萧萧兮夜漫漫”是空旷而又多风的西北地区的夜晚所给人的感受。这种感受由于“琵琶一曲”的演奏更加增强了、加重了。以上六句主要写环境背景。诗人吸取了民歌的艺术因素,运用顶针手法,句句用韵,两句一转,构成轻快的、咏唱的情调,写出凉州的宏大、繁荣和显明的地域色彩。最后一句“风萧萧兮夜漫漫”,用了一个“兮”字和叠词“萧萧”、“漫漫”,使节奏舒缓了下来。后面六句即正面展开对宴会的描写,不再句句用韵。
“河西幕中多故人,故人别来三五春。”这两句重复“故人”二字,见出情谊深厚。因为“多故人”,与诸友人见面离别的时间自然不尽相同,所以说“三五春”。“花门楼前见秋草,岂能贫贱相看老。”“花门楼”在这里即指凉州馆舍。两句接“故人别来三五春”,是说时光在流逝,花门楼作证吧,又到了秋天草黄的季节了。岁月催人,我们怎能互相看着在贫贱中老下去呢?言下之意是时不待我,大家要赶快建立功业。“一生大笑能几回,斗酒相逢须醉倒。”一个“笑”字,写出岑参和朋友们的本色。宴会中不时地爆发出大笑声,这样的欢会,这样的气氛,这样的大笑,一生中也难得有几回,老朋友们面对这个觥筹交错的难得机会,总得比一比吧,怎能不为之醉倒呢!
这首诗把边塞的生活情调和强烈的时代气息结合了起来。全诗由月照凉州开始,在着重表现边城风光的同时,不仅写出了那种月光照耀着的七里十万家和城中荡漾着的一片琵琶声,也鲜明地勾勒出了当时凉州繁华阔大的格局、和平安定的气氛、多民族和谐共处的场景。至于诗中所写的夜宴,更是兴会淋漓,充满豪气。“花门楼前见秋草,岂能贫贱相看老”,不是有感于时光流逝,叹老嗟卑,而是有着能够掌握自己命运的豪迈感,表现出“古人”们的奋发有为的人生态度。“一生大笑能几回”的“笑”,更是爽朗豪迈的笑,它来源于对未来、对生活的信心。同样,末句“须醉倒”,也不是借酒浇愁,而是以酒助兴,这种醉是豪迈乐观的醉,是相知互勉的醉。从人物的神态中,我们能够感受到盛唐时代强劲的脉搏。语言自然流畅,带有浓郁的边地特色,凸现出诗人向民歌学习的风格。
从岑参的这首诗我们可以看出,盛唐时期能够与洛阳、扬州、益州、广州等并列为全国第一流城市的凉州,市容繁华,人口众多,多民族共同生活,呈现出一派繁荣昌盛、和平安定的气象,人们尽可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共同为大唐帝国效力。而文人们的生活更具特色:他们生活在盛唐政治清明、经济发达、文化繁荣、思想解放的大背景下,没有动荡不安的忧危,没有文字狱的后怕,有的是支撑大厦、力挽狂澜的雄心壮志,有的是昂扬豪迈、建功立业的时代风格,他们在夜宴豪饮中,尽可以抒发自己的理想,尽可以展现自己的内心世界。
张翙笔下的凉州:物华人杰风犹在,弦歌之中谱升平
张翙(1750-?),字凤飏,号桐圃,清凉州府(今甘肃武威市)人。乾隆三十四年(1769)进士,授户部主事,累迁户部郎中,曾任江西吉安、湖北荆州、湖南长沙等地知府。工诗,各体皆备,著有《念初堂诗集》。
张翙有《凉州怀古》三首,第一首写历史无情,江山依旧;第二首在怀古颂今中,慨叹人生的短暂。第三首则以大视角、大境界、大手笔抒写凉州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诗曰:祁连磅礴拥孤城,文物当年似两京。二妙才华推索靖,六朝骚雅付阴铿。人龙卧后风犹在,金粟歌来角不鸣。中外即今同禹甸,好听弦诵谱升平。
这首怀古诗既不同于前面两首咏史诗,也不同于历代咏怀古人的诗歌,作者极写历史上的凉州物华天宝,人才辈出;而现在已经是升平之世,更应该培育人才,继承前贤,谱写盛世华章。
这首诗开笔不凡,确如古人所赞“起手如黄鹤高举,见天地方圆”(沈德潜语),打破了首句点题的俗套,运用俯瞰的视角,以浓墨重彩勾勒出一幅壮阔雄浑的图景:巍巍祁连山绵延千里,拥抱着古老的凉州城;这座城市在过去的岁月里,曾经是人文荟萃,物产丰富的名都大邑,就如同京城西安、洛阳一样。颔联紧承上句,写凉州不仅文物之盛,而且人才辈出,如索靖、阴铿,他们的才华在当时都是首屈一指的。颈联写像索靖、阴铿这样的杰出人物虽已去世,但他们的风范永存,光耀后世;如今已是太平盛世,年年五谷丰登,再也听不到战斗的号角了。尾联紧承上句,写如今天下一统,四海之内到处是一片歌颂升平的弦歌之声。言外之意是:如今太平盛世,更应该重视读书,培育人才,再写凉州辉煌篇章。
此诗大气磅礴,文采飞扬,盛赞凉州辉煌历史,启迪后人传承发扬优秀传统。音节高昂,节奏明快,以史为证,令人振奋。从张翙的这首诗可以看出,清代中叶的凉州也和全国一样,经济得到恢复发展,社会安定祥和,但隐藏在社会深处的各种矛盾已经凸显。所以,一些有识之士们清醒地认识到,(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在经济持续发展的同时,要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和人才培养,弘扬凉州优秀文化传统,续写升平乐章,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和谐发展。
沈翔笔下的凉州:山水相映竞风流,塞北江南古凉州
沈翔,清乾隆时人,其生平事迹不详。曾创作《凉州怀古》十首,通过对凉州历史上发生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的怀念和凭吊,兼写凉州山川地理、经济文化,表达对凉州的热爱之情。其一曰:山开地关结雄州,万派寒泉日夜流。峰向南来皆有雪,城当西面独无楼。市廛人语殊方杂,道路车声百货稠。塞北江南称此地,河西千里尽荒陬。

(祁连山麓)
这是一首七言律诗,在写景中寄托着怀古的幽思。前四句写凉州的地形。“山开地关结雄州”句写巍峨绵延的祁连山高耸入云,肥沃的土地辽阔无边,山地相连共同构成这雄伟壮阔的凉州。“开”“关”反映出凉州山、地的特征。“万派寒泉日夜流”句用夸张的手法写凉州大地上日夜奔流的河水。“万派”、“日夜”写凉州泉水遍布,流量充盈。“峰向南来皆有雪”句写作者眺望南山,见峰顶白雪皑皑。随后,作者将目光收回,由远及近,四望凉州城,发现唯独西城门没有城楼。“市廛人语殊方杂”两句写作者在城内看到的情景:熙熙攘攘的集市上,有来自不同地区和民族的人,他们操着不同的口语徜徉在市场上;道路上车马来来往往,马路两旁的摊位上和店铺里都摆满了货物。最后两句抒发作者的豪情。看到凉州如此繁华、热闹,不禁由衷地赞美道:千里河西走廊大多是荒凉贫瘠、人烟稀少的地方,唯独凉州似“塞北江南”,繁华无比。《汉书·地理志下》:“自武威以西……习俗颇殊,地广民稀。”
这首诗二、三两联对仗,十分工整凝练。三、四句以“皆有雪”与“独无楼”对比,一有一无,描写了凉州独特的地形;五、六句以“人语殊方杂”与“车声百货稠”对举,反映凉州的繁华。全诗情从景发,收束自然,韵致幽深。
从沈翔的这首诗可以看出,凉州山野之间泉水淙淙,雪映祁连,风光无限;市区之内车水马龙,人来人往,热闹非凡;市面上店铺林立,货物种类繁多,过往的人操着不同的口音进行交易,真正是市场繁荣,人烟稠密。作者真没有想到,在这荒凉的西北边陲,这里的城市生活还真有点塞北江南的光景呢!
张维翰笔下的凉州:昔日繁华的颂歌,今日苦难的写照
张维翰(1886-1979),字季勋,号莼沤,云南大关县人。早年毕业于云南法政学堂。曾参加辛亥革命,任云南都督府秘书,后加入国民党。1942年奉命视察河西,作《西北纪行杂咏》;1949年受聘于香港新亚书院,教授文史;1950年去台湾。晚年潜心学佛,监修大藏经。有《都市计划》《法制要论》《莼沤类稿》等。
1942年,作者在视察河西当中,目睹了凉州经济的萧条,人民生活的艰辛,在义愤难平之下写下了这首《凉州行》:物阜民殷岁有秋,武威大邑古凉州。十万力役殊憔悴,劳止当今赋小休。
与唐代诗人王建《凉州行》不同,仅从体裁来看,这是一首七言绝句。“物阜民殷岁有秋”两句,是对历史上凉州的繁华与富庶的赞叹。意为:凉州物产丰盛,百姓家家殷实。自古以来就显示出它的重要地位,不仅作为军事上的重镇屏障着汉唐古都长安,同时也是当时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驿站和商埠。尤其在盛唐时,“河西陇右三十三州,凉州最大,土沃物繁而人富足”(《新五代史》卷14);“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莫如陇右”(《资治通鉴》卷216)。故诗人在此热情讴歌“武威大邑古凉州”。三、四句,转而写到当时凉州的所见和所感。“十万力役殊憔悴”是诗人凉州行时的所见。抗日战争时期,为保证苏联援华物质顺利进入抗日前线,国民政府决定修建甘新公路,在武威的军阀马步青(时任陆军骑五军军长、甘新公路督办)借机征用大批百姓修建公路。作者给我们勾勒出这样一幅图景:数万名面容极其憔悴的老百姓在当局的压迫下,离开家园去修建公路,致使田园荒芜,民不聊生。“殊”是极其特别之意;“十万”是约数,形容人数极多。“劳止当今赋小休”是对执政当局的劝告,意思是说如今应当停止这种苦役,让人民休养生息才好。
全诗紧扣诗题“凉州行”,前两句诗人是对历史上辉煌武威的赞叹,后两句通过“行”,将所见用七个字表现出来,对当时凉州百姓真实的生活状况做了高度地概括,一方面揭露了国民政府的苛政,同时也对日本侵略者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表示极大的愤慨。
从张维翰的这首诗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由于抗日战争进入关键时期,加上政治腐败,官场黑暗,凉州已完全失去了往日“河西大邑”的风貌,经济凋敝,徭役沉重,老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从以上五首诗我们可以初步理出凉州古代都市生活由起步—繁华—落后的发展脉络:自汉代经魏晋到五凉的准备,北魏时的凉州已初具大都市的气派,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盛唐时的凉州,是西北仅次于长安的通都大邑,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官员和文人们建功立业、多民族融合之地;清代的凉州虽然大逊于盛唐,但仍不失河西走廊的繁华之都;而民国时期的凉州,在兵荒马乱和多种天灾人祸的洗劫下,昔日“物阜民殷”的“大凉州”风采尽失,完全是一个非常落后的边州了。这是凉州发展的缩影,也是旧中国发展的缩影。
“英雄都已归黄土,明月依旧古凉州”(清·王永清)。明月永恒,凉州依旧,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在这片英雄的土地上,孕育着新的希望,期望着新的辉煌。凉州的发展,凉州的振兴,凉州的崛起,在改革开放的节拍中才能变为现实。惟愿我们再创凉州辉煌!
 关注凉州文化研究微信公众号
关注凉州文化研究微信公众号Copyright © 2018 www.lzwenhuawang.com 主办:武威市凉州文化研究院
陇ICP备18003089号-2 技术支持:甘肃天问信息咨询有限责任公司